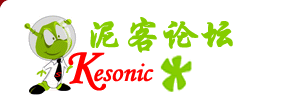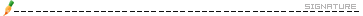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可是,狗吊岩村实在太穷太苦了。不仅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而且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靠油灯照明,连寄一封信也要走18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找到邮所。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心理和话语障碍又使他们久久不能融入这个环境。追随他的志愿者一个一个地离去。
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会后,他又返回了狗吊岩村,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
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会后,他又返回了狗吊岩村,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